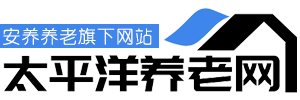原创 收集故事的人 故事FM
爱哲按:
4 月 2 日是「世界孤独症日」。孤独症也会被叫做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性障碍。
孤独症人常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常常无法流畅表达自己,也不明白普通人在社交当中的规则,不熟悉他们的人,很难走近、理解他们。
对于多数,尤其是程度较重的孤独症人,他们终身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一直会需要照料和陪伴。
「星星的孩子」也会慢慢长大,而陪伴着他们成长的人,这一路走来都经历过什么坎坷?
老马,27岁孤独症人的爸爸
今天我们的第一位讲述者,今年 62 岁的老马,给我们讲了一个他和孤独症儿子马昕在旅行途中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去贵州玩儿,那儿有山有水,马昕很高兴。我们去徒步、爬山,马昕一个 23 岁的大小伙子,体力好,总跑在我前头,很快就走出我的视线了。
我就在后面慢慢走,每次走到山路的一个拐弯处,就能看见他坐在那儿等我。一看到我,他就又接着走远了。在海边散步也是,他看到我落在后面,就会走回来拉着我。有时候胳膊搭在我肩膀上,俩人一块儿走。出门在外,有重的东西从来都是马昕背着。
那回我第一次感觉到儿子长大了。他不会跟着别人瞎跑,他心里有我,知道要等着我。
-1-
「相依为命」的时光
旅行的想法是我在 2016 年做一个心脏手术期间想到的。术前检查的等待时间很长,我躺在床上无所事事,想着自己忙忙碌碌了几十年,好不容易儿子一天天长大,我能陪他的时间也一天比一天少了。
当病人的感觉是很微妙的,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很无助,意识到很多事情都无法左右。我已经 57 了,之后有能力、体力、精力的时间更有限了,要是再不好好陪陪马昕的话,等到我真的动不了的时候,我应该会有遗憾。
儿子确诊后的这二十几年里,一直是我带着他,东奔西跑,到机构做各种各样的康复训练,矫正他的刻板行为,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填鸭子一样。一直没能从生活小事上多给他一些爱,培养一下父子感情,也没能带他去看看祖国的山河大川。
如果马昕不是个孤独症孩子,我们俩能像哥们儿一样。但是他的情况不允许我当他的哥们儿,我做父亲的必须得照顾好他。
手术之后我身体恢复得还可以,我想趁这时间尽早带他到处玩玩。我不填鸭子了,我也不要求他学这学那了,我就想告诉他,山很漂亮,天很蓝,我要告诉他大树在哪儿。
在他妈妈的支持下,我们父子一起度过了这么一段「相依为命」的时光。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两年半的疫情,真讨厌,没有它,我们爷儿俩指不定又到哪儿玩去了。

■ 老马和儿子马昕
-2-
一个「安乐窝」
前段时间我们以马昕的名义租了一套 40 平米的一居室,他今年 27 岁了,每天跟我一起赶早市、下楼遛弯儿,和社区周围的人打交道。我现在还有点舍不得他,但再过个五年十年,我可能会考虑给他找一个「安乐窝」。
不是说江湖上随便一个养老福利机构,能管吃管喝就行了,我要找的是了解和接纳孤独症人的机构。因为他是大龄孤独症人了,一方面需要的是养护,另一方面是需要做点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倒不是奢望他能有个职业,挣多少钱。如果人家问他:「马昕你干嘛呢?」「做工作,做两块小蛋糕。」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心里头特暖。
这仅仅是「设想」,之后的几年会发生什么,能不能找到设想中的「安乐窝」,老马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时间不等人, 孤独症家长的孩子终有一天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
田惠萍,36岁孤独症人的妈妈
我叫田惠萍,我的儿子叫杨弢,他是一位 36 岁的孤独症人。
田惠萍是一位 50 后。在 80 年代末,她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帮助孤独症儿童家庭的非营利组织,北京星星雨,也将提升孤独症人生活质量的行为训练引入中国。田惠萍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创业者,或者孤独症教育专家,她只是一位孤独症人的母亲。
杨弢「老无所养」的恐慌,从他被诊断那一天就开始了。
因为我知道,我会老会死,孩子以后指望不上我。人要有远虑,才有近忧。我的追求是:有一天我不在了,没有抚养能力了,杨弢也能够顺利、平静、有尊严地生活。为了实现这个追求,成天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和求神拜佛,都是没有用的。
我要让我的孩子好养好带,既被家里人接受,也能被外人接纳。我希望,就算有一天让没有照料孤独症经验的普通人来照顾他也没有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你知道我做了多少准备吗?
-1-
从坐公交开始的准备
1993 年,我跟杨弢在北京挤公交。
杨弢一生下来就有 8 斤重,一直都是个大胖小子,而我不是一个体格壮硕的妈妈。他小的时候抱他上公交车,别人都会让座,但当他长到那种半高不矮的时候,麻烦就来了。
有一次周末我带他上公交车,上去以后没有人给他让座,于是杨弢一屁股就坐在了一个小伙子的腿上。这就是孤独症人,这就是他们学习的社交规则,刻板就是他们的症状之一。
那时候杨弢才 8 岁,小伙子只是觉得有点难为情就会让他坐。但因为我对孤独症的本质有非常清晰的认知,我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就想如果他 18 岁了还这样会怎样?如果是一个女孩会怎样?
那天是一个周末,我第二站就带着杨弢下了车。那时候,北京西三环上有三、四路公共汽车,我管它哪一路,我也不在乎我们原来要去哪了,我看到一辆没座位的车来了就带他上去。
当孤独症人一开始不会社会规范的时候,我就要帮他做到,我就拽着他,让他扶着车座的后背,夸他「真棒!」告诉他这样做是对的,然后就下车,这样的训练叫一个回合。等下一辆车来了再上去,下一站我们再下车。有的孩子只需要连续三个回合就能明白,有的孩子需要连续训练三个月。这种方法让杨弢在三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挂着月票坐公交。
你以为这样就很顺利了吗?
有一次我带着他坐公交车,北京那时候还是长公交,前后有两个车厢。先开始很棒,他能抓住椅子背站着。但这个时候,前面车厢有一个人到站了,站起来要下车,因为隔得比较远,我都没注意到前面有空出来的座,可这时候,杨弢就「排山倒海」地拨开人群去坐。因为他学习到的规则就是「有人站起来了我就去坐」,所以一定要穿越人群找到座位坐下。
这事儿就又提醒了我——有一系列的社会交往规则制约着我们每个人的行为,而孤独症患者意识不到这点。因此,我就从生活的点滴开始训练他应该怎么做。
到现在,公交上的社会规则杨弢的行为可以达到非常规范的程度。他一上去不会再去抓椅背,而是先抓着中间的杠子或者吊环,先把自己站稳了,如果他旁边有人站起来了,你知道他会怎么做吗 ?他会等一下,看没有别的人坐,他才坐下去。
这是当年我抱着他挤公交的时候就在所有生活细节里做的准备。这才能有今天,我带着杨弢出门旅行时,每一个环节都能克服。

■ 田惠萍带着杨弢旅游
-2-
我不在了,怎么办?
在与孩子的漫长互动中,我将杨弢培养成了一个生活基本自理的人。但我想,虽然杨弢现在很好带了,但我也不能照顾他一辈子,以后杨弢谁来带?
我 2010 年开始想这件事,2012 年就起草了第一份遗嘱,关于我死了以后,杨弢交给谁照料,以及财政交给谁管理的问题。每次我写遗嘱,星星雨都有备案,我去世之后就能启动,有人知道怎么开我们家的保险柜,以及我遗嘱的位置。我才 50 多岁的时候就把这些事安排好了,因为后事还不趁你年轻思路最清晰的时候去设计,我不能等死了把孩子突然给一个什么人吧?
但是,当时律师朋友跟我说,这遗嘱合情合理不合法。因为并不是你想把孩子托给谁照顾,就能让谁照顾的。托付人必须属于家庭成员,比如兄弟姐妹、侄儿侄女这类亲属。但是作为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杨弢已经 20 多年没有跟父亲那边的人打过交道了。
那是一些我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杨弢的人,我的信任感肯定会降低。但是他们拿到监护权同时就拿到了我给杨弢留下的遗产。后来民法典终于给了我一个机会,一个我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合法的指定谁监护杨弢的机会。
2021 年初,新修订的《民法典》确立生效,其中完善了"成年意定监护制度"。也就是,针对杨弢这样的只拥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根据《民法典》第二十九条,我就可以通过遗嘱,指定我信任的人或组织成为儿子的监护人。
民法典的改变对我遗嘱的安排是水到渠成的。民法典给了我们安排孩子未来人生的机会。我们要在孩子很早的时候,就给他资源,让别人有机会了解他、走进他,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被别人喜欢、热爱和接纳。
2021 年,在众多心智障碍者家属的推动下,国内几家信托机构设立了特殊需要信托。原本信托是一种门槛挺高的理财方式,需要投入大量启动资金,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但是慈善信托降低了资金的进入门槛。特殊需要信托刚一推出,田惠萍就签下了一份信托协议。这样一来,监护权和财产权也分开了,监护人为孩子做决定,信托机构负责给钱,这样有效确保遗产都是用在了和孩子有关的支出上。
这种权和钱的分割是好事,捆绑人性就是愚昧的行为,真正科学的就是责权的分割。中国给有心智障碍的特殊需要人群设立信托账户,这样,我就可以把给杨弢的钱存进信托账户,我不在了之后,整套体系可以运行起来。
我把杨弢的生活管理团队,称作杨弢生活助援团。他们有工作会议、报销和管理制度,能够规划杨弢白天和晚上的日程,这样,杨弢的生活链条就闭合了,一块拼板也就合上了。
田惠萍用了半辈子时间将杨弢培养成了一个普通人也能带的孤独症人。又在70多岁的时候终于等来法律晚上和特殊信托。唯独还有一个遗憾:杨弢往后漫长的人生要做点什么呢?
现在,杨弢白天在家可以帮我做事情。所以最重要的是,他的生活要有内容,不一定是所谓的工作,但有些东西我不抱希望,我只是想做到我不在以后,会有人好好照顾他。
当照料者和遗产问题都有了相应的的解决方案,大龄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开始想攻克另一个难关:他们已经成年的孩子不仅是要存活,更要生活,要有自己的追求和热爱。
余华,27岁孤独症人的妈妈
我是余华,今年 53 岁,我有一个 27 岁儿子,叫小满,是个中重度的孤独症人。
小满 18 岁从培智学校毕业以后,我就一直在尝试解决大龄孤独症人的安置难题。我和另外 5 位妈妈一起创办了一家「日间学校」, 让孩子们能在专业人士的辅导和陪伴下拥有丰富的日间生活,这样他们白天就有了新的去处,不必被养在家里。
但「日间学校」的模式也不是长久之计。那时候学校离我家有点远,每天要开三小时的车接送小满上下课,还要照顾相继病倒的父母。这种奔波的状态持续时间长了,不光我感觉身心俱疲,小满也出现了情绪和睡眠问题。
我妈妈在去世之前,神志清楚的时候,还一直挂念着小满,她担心如果她不在了,没人能更好地帮助我了。实际上妈妈生病的时候也不过六十八九岁,年龄不算很大。
她的离开让我突然意识到,没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遇到疾病、死亡。当它们一旦来了,就算你自身的力量再强、再先进的医疗水平可能都无法阻挡。我有一天肯定也会老,也会生病,严重到了一定程度,我不但没有能力照顾自己,也会没有能力照顾小满。
我不得不往更长远了想:如果有一天我也离开了,小满怎么办?
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小满在没有我陪伴的情况下也能长期、稳定的生活?
-1-
「榉之乡」
我考察过一些养护机构,但它们有的日常活动不够丰富,有的房子是租来的、甚至出过被要求搬走的风波,这些都让我没办法托付。
我心目当中理想的地方是日本的「榉之乡」,那是一家针对成年孤独症人的养护设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 21 位家长筹资创办。我在 2009 年实地拜访过一次,那里孤独症人的生活状态,让我非常惊讶。
当时有一个 50 多岁的女士,她的程度很重,生理期的时候情绪爆发,会有打头这样的行为。但在她情绪平稳之后,还是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在一个废品分类的车间工作,负责用机器把易拉罐压扁。
这个工作很简单,但看到程度那么重的孤独症人都可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让我感觉特别好。
我觉得我的孩子有希望了。让他在这样的机构里面很有尊严地生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是我的梦想。

■ 日本「榉之乡」/ ins@keyakinosato
-2-
给孩子们一个「永久的家」
2017 年国庆节,我们一家三口回到小满爸爸的老家,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我们发现这个曾经的贫困县有了很大变化:县城里有了高速路,通了高铁,可以直达合肥、武汉、上海和南京;环境也被保护得很好。那里被誉为「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植被茂盛,一眼望去是整片的绿色。
我们带小满回来待了大概八九天的时间,他在这里很放松。
原来比较常有的一些刻板行为,比如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手部的一些重复性动作,还有情绪爆发时候的又跳又叫都减少了。他会很安静,也开始关注周围,睡眠也好了。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带他回来住一段时间。
我在老县城边上租下了一所闲置的希望小学。重新装修期间,几个孤独症家庭来金寨玩,家长们觉得这个地方不仅适合孩子们生活,也特别适合他们养老。因为这样的契机,我们打算在金寨建造梦想中给孩子的那个「永久的家」。

 ■ 小满和伙伴在金寨
■ 小满和伙伴在金寨
我们给这个家起名为「金寨星星小镇」,将会是一个由孤独症家庭共同投资、建设、运营的成年孤独症生活养老社区。在我们的规划下,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小镇里生活、就业、养老。他们有专业人士进行看护陪伴,家长们可以放心离开,也可以选择住进「家长公寓」近距离陪伴孩子。
在这之前,我们在国内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我们也不可能等。再等十年、二十年,等到我老了,七八十岁了,就没有能力再去做这样的事情了。与其让自己二十年都活在焦虑状态里边,等待将来有人来做这件事,不如我们趁现在自己开始做。这其实也是我们化解焦虑的一个方式。
星星小镇的运营采取公司制,家长们以股东的身份加入小镇,每个家庭都需要提供 500 万元以上的资产证明,一起投资建设。股东的孩子可以取得小镇的永久居住权,得到终身照顾。
小镇已经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土地,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明年年初就可以入住。在等待星星小镇建设的过程中,那所重新装修过的希望小学成了星星小镇的实验基地——星星家园。
从 2017 年起,已经有包括小满在内的 18 个我们前期股东家庭的孩子住进了星星家园,他们在几位专业辅导老师的陪伴下提前适应星星小镇的集体生活模式。他们会按规定好的时间表练习生活自理能力,进行户外运动,学习切菜、烘焙等技能,享受自己的爱好。

 ■ 孩子们在星星家园
■ 孩子们在星星家园
我们之所以这么早为孩子做准备,实际上是希望他们和周围的伙伴和老师建立好关系。如果有一天,他的父母不能再照顾他了,甚至是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们还有周围人的支持,还能很好地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目前许多像星星雨、星星小镇这样的公益组织都在为大龄孤独症人的养老问题积极地准备着解决方案,我们也希望能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解孤独症人,一起为他们创造一个安全、平等、有尊严的未来 。
参考资料
1、《重磅 | 小镇答疑篇来啦!》,金寨星星小镇,2021.07.18
-封面图及文中未注明来源图片
均由 讲述者 提供
爱哲按:
4 月 2 日是「世界孤独症日」。孤独症也会被叫做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性障碍。
孤独症人常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常常无法流畅表达自己,也不明白普通人在社交当中的规则,不熟悉他们的人,很难走近、理解他们。
对于多数,尤其是程度较重的孤独症人,他们终身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一直会需要照料和陪伴。
「星星的孩子」也会慢慢长大,而陪伴着他们成长的人,这一路走来都经历过什么坎坷?
老马,27岁孤独症人的爸爸
今天我们的第一位讲述者,今年 62 岁的老马,给我们讲了一个他和孤独症儿子马昕在旅行途中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去贵州玩儿,那儿有山有水,马昕很高兴。我们去徒步、爬山,马昕一个 23 岁的大小伙子,体力好,总跑在我前头,很快就走出我的视线了。
我就在后面慢慢走,每次走到山路的一个拐弯处,就能看见他坐在那儿等我。一看到我,他就又接着走远了。在海边散步也是,他看到我落在后面,就会走回来拉着我。有时候胳膊搭在我肩膀上,俩人一块儿走。出门在外,有重的东西从来都是马昕背着。
那回我第一次感觉到儿子长大了。他不会跟着别人瞎跑,他心里有我,知道要等着我。
-1-
「相依为命」的时光
旅行的想法是我在 2016 年做一个心脏手术期间想到的。术前检查的等待时间很长,我躺在床上无所事事,想着自己忙忙碌碌了几十年,好不容易儿子一天天长大,我能陪他的时间也一天比一天少了。
当病人的感觉是很微妙的,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很无助,意识到很多事情都无法左右。我已经 57 了,之后有能力、体力、精力的时间更有限了,要是再不好好陪陪马昕的话,等到我真的动不了的时候,我应该会有遗憾。
儿子确诊后的这二十几年里,一直是我带着他,东奔西跑,到机构做各种各样的康复训练,矫正他的刻板行为,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填鸭子一样。一直没能从生活小事上多给他一些爱,培养一下父子感情,也没能带他去看看祖国的山河大川。
如果马昕不是个孤独症孩子,我们俩能像哥们儿一样。但是他的情况不允许我当他的哥们儿,我做父亲的必须得照顾好他。
手术之后我身体恢复得还可以,我想趁这时间尽早带他到处玩玩。我不填鸭子了,我也不要求他学这学那了,我就想告诉他,山很漂亮,天很蓝,我要告诉他大树在哪儿。
在他妈妈的支持下,我们父子一起度过了这么一段「相依为命」的时光。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两年半的疫情,真讨厌,没有它,我们爷儿俩指不定又到哪儿玩去了。


■ 老马和儿子马昕
-2-
一个「安乐窝」
前段时间我们以马昕的名义租了一套 40 平米的一居室,他今年 27 岁了,每天跟我一起赶早市、下楼遛弯儿,和社区周围的人打交道。我现在还有点舍不得他,但再过个五年十年,我可能会考虑给他找一个「安乐窝」。
不是说江湖上随便一个养老福利机构,能管吃管喝就行了,我要找的是了解和接纳孤独症人的机构。因为他是大龄孤独症人了,一方面需要的是养护,另一方面是需要做点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倒不是奢望他能有个职业,挣多少钱。如果人家问他:「马昕你干嘛呢?」「做工作,做两块小蛋糕。」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心里头特暖。
这仅仅是「设想」,之后的几年会发生什么,能不能找到设想中的「安乐窝」,老马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时间不等人, 孤独症家长的孩子终有一天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
田惠萍,36岁孤独症人的妈妈
我叫田惠萍,我的儿子叫杨弢,他是一位 36 岁的孤独症人。
田惠萍是一位 50 后。在 80 年代末,她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帮助孤独症儿童家庭的非营利组织,北京星星雨,也将提升孤独症人生活质量的行为训练引入中国。田惠萍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创业者,或者孤独症教育专家,她只是一位孤独症人的母亲。
杨弢「老无所养」的恐慌,从他被诊断那一天就开始了。
因为我知道,我会老会死,孩子以后指望不上我。人要有远虑,才有近忧。我的追求是:有一天我不在了,没有抚养能力了,杨弢也能够顺利、平静、有尊严地生活。为了实现这个追求,成天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和求神拜佛,都是没有用的。
我要让我的孩子好养好带,既被家里人接受,也能被外人接纳。我希望,就算有一天让没有照料孤独症经验的普通人来照顾他也没有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你知道我做了多少准备吗?
-1-
从坐公交开始的准备
1993 年,我跟杨弢在北京挤公交。
杨弢一生下来就有 8 斤重,一直都是个大胖小子,而我不是一个体格壮硕的妈妈。他小的时候抱他上公交车,别人都会让座,但当他长到那种半高不矮的时候,麻烦就来了。
有一次周末我带他上公交车,上去以后没有人给他让座,于是杨弢一屁股就坐在了一个小伙子的腿上。这就是孤独症人,这就是他们学习的社交规则,刻板就是他们的症状之一。
那时候杨弢才 8 岁,小伙子只是觉得有点难为情就会让他坐。但因为我对孤独症的本质有非常清晰的认知,我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就想如果他 18 岁了还这样会怎样?如果是一个女孩会怎样?
那天是一个周末,我第二站就带着杨弢下了车。那时候,北京西三环上有三、四路公共汽车,我管它哪一路,我也不在乎我们原来要去哪了,我看到一辆没座位的车来了就带他上去。
当孤独症人一开始不会社会规范的时候,我就要帮他做到,我就拽着他,让他扶着车座的后背,夸他「真棒!」告诉他这样做是对的,然后就下车,这样的训练叫一个回合。等下一辆车来了再上去,下一站我们再下车。有的孩子只需要连续三个回合就能明白,有的孩子需要连续训练三个月。这种方法让杨弢在三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挂着月票坐公交。
你以为这样就很顺利了吗?
有一次我带着他坐公交车,北京那时候还是长公交,前后有两个车厢。先开始很棒,他能抓住椅子背站着。但这个时候,前面车厢有一个人到站了,站起来要下车,因为隔得比较远,我都没注意到前面有空出来的座,可这时候,杨弢就「排山倒海」地拨开人群去坐。因为他学习到的规则就是「有人站起来了我就去坐」,所以一定要穿越人群找到座位坐下。
这事儿就又提醒了我——有一系列的社会交往规则制约着我们每个人的行为,而孤独症患者意识不到这点。因此,我就从生活的点滴开始训练他应该怎么做。
到现在,公交上的社会规则杨弢的行为可以达到非常规范的程度。他一上去不会再去抓椅背,而是先抓着中间的杠子或者吊环,先把自己站稳了,如果他旁边有人站起来了,你知道他会怎么做吗 ?他会等一下,看没有别的人坐,他才坐下去。
这是当年我抱着他挤公交的时候就在所有生活细节里做的准备。这才能有今天,我带着杨弢出门旅行时,每一个环节都能克服。


■ 田惠萍带着杨弢旅游
-2-
我不在了,怎么办?
在与孩子的漫长互动中,我将杨弢培养成了一个生活基本自理的人。但我想,虽然杨弢现在很好带了,但我也不能照顾他一辈子,以后杨弢谁来带?
我 2010 年开始想这件事,2012 年就起草了第一份遗嘱,关于我死了以后,杨弢交给谁照料,以及财政交给谁管理的问题。每次我写遗嘱,星星雨都有备案,我去世之后就能启动,有人知道怎么开我们家的保险柜,以及我遗嘱的位置。我才 50 多岁的时候就把这些事安排好了,因为后事还不趁你年轻思路最清晰的时候去设计,我不能等死了把孩子突然给一个什么人吧?
但是,当时律师朋友跟我说,这遗嘱合情合理不合法。因为并不是你想把孩子托给谁照顾,就能让谁照顾的。托付人必须属于家庭成员,比如兄弟姐妹、侄儿侄女这类亲属。但是作为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杨弢已经 20 多年没有跟父亲那边的人打过交道了。
那是一些我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杨弢的人,我的信任感肯定会降低。但是他们拿到监护权同时就拿到了我给杨弢留下的遗产。后来民法典终于给了我一个机会,一个我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合法的指定谁监护杨弢的机会。
2021 年初,新修订的《民法典》确立生效,其中完善了"成年意定监护制度"。也就是,针对杨弢这样的只拥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根据《民法典》第二十九条,我就可以通过遗嘱,指定我信任的人或组织成为儿子的监护人。
民法典的改变对我遗嘱的安排是水到渠成的。民法典给了我们安排孩子未来人生的机会。我们要在孩子很早的时候,就给他资源,让别人有机会了解他、走进他,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被别人喜欢、热爱和接纳。
2021 年,在众多心智障碍者家属的推动下,国内几家信托机构设立了特殊需要信托。原本信托是一种门槛挺高的理财方式,需要投入大量启动资金,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但是慈善信托降低了资金的进入门槛。特殊需要信托刚一推出,田惠萍就签下了一份信托协议。这样一来,监护权和财产权也分开了,监护人为孩子做决定,信托机构负责给钱,这样有效确保遗产都是用在了和孩子有关的支出上。
这种权和钱的分割是好事,捆绑人性就是愚昧的行为,真正科学的就是责权的分割。中国给有心智障碍的特殊需要人群设立信托账户,这样,我就可以把给杨弢的钱存进信托账户,我不在了之后,整套体系可以运行起来。
我把杨弢的生活管理团队,称作杨弢生活助援团。他们有工作会议、报销和管理制度,能够规划杨弢白天和晚上的日程,这样,杨弢的生活链条就闭合了,一块拼板也就合上了。
田惠萍用了半辈子时间将杨弢培养成了一个普通人也能带的孤独症人。又在70多岁的时候终于等来法律晚上和特殊信托。唯独还有一个遗憾:杨弢往后漫长的人生要做点什么呢?
现在,杨弢白天在家可以帮我做事情。所以最重要的是,他的生活要有内容,不一定是所谓的工作,但有些东西我不抱希望,我只是想做到我不在以后,会有人好好照顾他。
当照料者和遗产问题都有了相应的的解决方案,大龄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开始想攻克另一个难关:他们已经成年的孩子不仅是要存活,更要生活,要有自己的追求和热爱。
余华,27岁孤独症人的妈妈
我是余华,今年 53 岁,我有一个 27 岁儿子,叫小满,是个中重度的孤独症人。
小满 18 岁从培智学校毕业以后,我就一直在尝试解决大龄孤独症人的安置难题。我和另外 5 位妈妈一起创办了一家「日间学校」, 让孩子们能在专业人士的辅导和陪伴下拥有丰富的日间生活,这样他们白天就有了新的去处,不必被养在家里。
但「日间学校」的模式也不是长久之计。那时候学校离我家有点远,每天要开三小时的车接送小满上下课,还要照顾相继病倒的父母。这种奔波的状态持续时间长了,不光我感觉身心俱疲,小满也出现了情绪和睡眠问题。
我妈妈在去世之前,神志清楚的时候,还一直挂念着小满,她担心如果她不在了,没人能更好地帮助我了。实际上妈妈生病的时候也不过六十八九岁,年龄不算很大。
她的离开让我突然意识到,没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遇到疾病、死亡。当它们一旦来了,就算你自身的力量再强、再先进的医疗水平可能都无法阻挡。我有一天肯定也会老,也会生病,严重到了一定程度,我不但没有能力照顾自己,也会没有能力照顾小满。
我不得不往更长远了想:如果有一天我也离开了,小满怎么办?
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小满在没有我陪伴的情况下也能长期、稳定的生活?
-1-
「榉之乡」
我考察过一些养护机构,但它们有的日常活动不够丰富,有的房子是租来的、甚至出过被要求搬走的风波,这些都让我没办法托付。
我心目当中理想的地方是日本的「榉之乡」,那是一家针对成年孤独症人的养护设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 21 位家长筹资创办。我在 2009 年实地拜访过一次,那里孤独症人的生活状态,让我非常惊讶。
当时有一个 50 多岁的女士,她的程度很重,生理期的时候情绪爆发,会有打头这样的行为。但在她情绪平稳之后,还是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在一个废品分类的车间工作,负责用机器把易拉罐压扁。
这个工作很简单,但看到程度那么重的孤独症人都可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让我感觉特别好。
我觉得我的孩子有希望了。让他在这样的机构里面很有尊严地生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是我的梦想。


■ 日本「榉之乡」/ ins@keyakinosato
-2-
给孩子们一个「永久的家」
2017 年国庆节,我们一家三口回到小满爸爸的老家,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我们发现这个曾经的贫困县有了很大变化:县城里有了高速路,通了高铁,可以直达合肥、武汉、上海和南京;环境也被保护得很好。那里被誉为「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植被茂盛,一眼望去是整片的绿色。
我们带小满回来待了大概八九天的时间,他在这里很放松。
原来比较常有的一些刻板行为,比如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手部的一些重复性动作,还有情绪爆发时候的又跳又叫都减少了。他会很安静,也开始关注周围,睡眠也好了。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带他回来住一段时间。
我在老县城边上租下了一所闲置的希望小学。重新装修期间,几个孤独症家庭来金寨玩,家长们觉得这个地方不仅适合孩子们生活,也特别适合他们养老。因为这样的契机,我们打算在金寨建造梦想中给孩子的那个「永久的家」。

 ■ 小满和伙伴在金寨
■ 小满和伙伴在金寨我们给这个家起名为「金寨星星小镇」,将会是一个由孤独症家庭共同投资、建设、运营的成年孤独症生活养老社区。在我们的规划下,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小镇里生活、就业、养老。他们有专业人士进行看护陪伴,家长们可以放心离开,也可以选择住进「家长公寓」近距离陪伴孩子。
在这之前,我们在国内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我们也不可能等。再等十年、二十年,等到我老了,七八十岁了,就没有能力再去做这样的事情了。与其让自己二十年都活在焦虑状态里边,等待将来有人来做这件事,不如我们趁现在自己开始做。这其实也是我们化解焦虑的一个方式。
星星小镇的运营采取公司制,家长们以股东的身份加入小镇,每个家庭都需要提供 500 万元以上的资产证明,一起投资建设。股东的孩子可以取得小镇的永久居住权,得到终身照顾。
小镇已经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土地,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明年年初就可以入住。在等待星星小镇建设的过程中,那所重新装修过的希望小学成了星星小镇的实验基地——星星家园。
从 2017 年起,已经有包括小满在内的 18 个我们前期股东家庭的孩子住进了星星家园,他们在几位专业辅导老师的陪伴下提前适应星星小镇的集体生活模式。他们会按规定好的时间表练习生活自理能力,进行户外运动,学习切菜、烘焙等技能,享受自己的爱好。

 ■ 孩子们在星星家园
■ 孩子们在星星家园我们之所以这么早为孩子做准备,实际上是希望他们和周围的伙伴和老师建立好关系。如果有一天,他的父母不能再照顾他了,甚至是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们还有周围人的支持,还能很好地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目前许多像星星雨、星星小镇这样的公益组织都在为大龄孤独症人的养老问题积极地准备着解决方案,我们也希望能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解孤独症人,一起为他们创造一个安全、平等、有尊严的未来 。
参考资料
1、《重磅 | 小镇答疑篇来啦!》,金寨星星小镇,2021.07.18
-封面图及文中未注明来源图片
均由 讲述者 提供
免责声明:本网资源来自网络,不代表安养网的观点和立场,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父母老去后,孤独症孩子怎么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