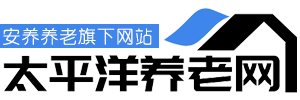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采访并文:赖嘉柔 韩倩倩 陈雪映 林嘉敏 许敏静 姜晓雪 陈婉雯
指导老师:尹连根 曾温娜
编辑:林子尧
编者按:
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比2010年上升了5.44%。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这代表着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随着家庭的养老功能部分向社会转移,养老院成为许多老人的选择。
本文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同学们的毕设作品,他们深入深圳的两家养老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与老人们共同生活。以解答心中的疑惑——养老院可以成为老人真正的“家”吗?
“长者之家”“安心家”“温馨之家”……在宣传中,养老院总是被塑以“家”的形象,甚至院名就带有“家”这一字。
何为家?
《说文解字》道:“家,居也。”但“家”的词义演变至今,早已不单有物理空间上的意义,而是衍生出了血脉联系、情感寄托、乡情民风等涵义。
谢民韬把到市场买菜,称为“上街玩”。在老家,他喜欢在早餐后“上街玩”,得空了就坐下来看看电视。虽也是简单重复的生活,但有亲朋好友在,一起喝两杯,“日子就好过了”。他说不清什么样算是“家”,只觉得在老家,“有家庭温暖,舒服。”
 一位常坐轮椅的老人撑着栏杆站起来朝窗户外望去。林嘉敏摄
一位常坐轮椅的老人撑着栏杆站起来朝窗户外望去。林嘉敏摄
章萍则认为“家”意味着“团圆”,而如今住进养老院,“团圆不了了”。老年人对“家”的观念,渗透着他们过往的经历和当下的处境,勾连起他们最深的记忆与最执着的想象。
正因为“家”是如此复杂的实体与观念的集合体,养老院固然如上一章所展示的,对有些人的确是“家”的所在,但对另外一些老人来说,真正的家与养老院,所隔的不止那一层围墙。
“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一到午餐或晚餐时间,护理员魏姐从她的房间里探出头来,朝对面喊一句:“谢民韬,拿杯来。”这时,谢民韬进房,出来时手上多了个不锈钢杯子。他大跨步走到莫姐门口,等她从一个大金龙鱼油罐大小的塑料容器里,倒出几小口酒来。
谢民韬爱喝酒,也爱抽烟。他常常搬了两张椅子在房门口,一张自己坐着,一张放个铁碗,作为烟灰缸。他自知吸烟有害健康,但从未想过戒烟,“好像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有时他话说多了,会用力咳好几声,但也不影响他下此结论。
谢民韬房间里两位老人刚搬来不久,他们入住后,谢民韬除了睡觉,很少回房间。他常左手提着水壶,右手夹着烟,在食堂和走廊间来回晃悠。我在门口遇到了谢民韬一位室友,他似乎不知道我常到这个房间来找谢民韬,热情地邀请我进屋看电视。提到谢民韬时,他小声说:“那人是个烟鬼。”
谢民韬曾因吸烟与之前的室友闹过矛盾。那时,谢民韬在房间里抽烟,他的室友拿了鞋示意要打他。不能在房间里抽烟,谢民韬便搬到了房门口,谁料旁边正巧是食堂的窗户,室友坐在里边,闻见烟味,伸出拐杖,作势要打人。谢民韬一把夺走拐杖,扔到了走廊的地上。
“要是在家乡,老子给他两拳。”谢民韬说着,挥舞起拳头。
谢民韬有一股乡村老汉的“野劲”。同我讲故事时,似乎总好强地想展现出他“不好惹”的一面。但如他的护理员所说,谢民韬不是不讲理的人。又或者说,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不合理的那一个,他甚至觉得“连烟都不抽,算什么男人家”。但是,他需要迁就这里的文明。
 谢民韬在走廊上吸烟。 林嘉敏摄
谢民韬在走廊上吸烟。 林嘉敏摄
谢民韬所在的四楼,居住的多半是半失能、失智老人,像谢民韬这样全自理的老人很少。谢民韬这样形容他们:“不抽烟也不喝酒,整天守着电视,等着吃饭时间,小妹(护理员)把饭打好送到面前。那样的日子……我都佩服。”
有一天,我刚与谢民韬交谈了二十分钟,他突然说:“今天你来了,看得起我,跟我说了这么多话,我平时起码要两三天才能说这么多话……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在这里,孤苦伶仃。”语毕,他少有地陷入沉默中。
谢民韬的老家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区,那是湖南、广东、广西三省交界的地方。他在那里生活了七十多年,出了门口到街上都是熟人。在家乡,不仅没有人管他抽烟喝酒,亲戚朋友还常邀请他去做客,一起喝酒。也正是这样,谢民韬唯一的女儿不放心78岁的父亲独自待在老家,怕他酒喝多了。在把母亲接到深圳带孩子后,也把他接到家中。住了不到两个月,谢民韬喝多了酒,和亲家“干起来”了。最后,女儿只得把他送到养老院。
福寿园董事长严敏称,目前院里百分之八九十的老年人来自外地,因子女在深圳工作、生活而被接来。同样被孩子接到深圳,又送进养老院的邱培雄说:“思想上经常还是想我的老家。”而当我们问起住得是否适应时,他第一反应不是直接回答,只哈哈笑几声道:“控制一下自己,为了子女,不要麻烦子女。”
除夕那天,谢民韬讲起了在老家过年的情景。糍粑、蒸酒、“跑油锅”的食物,要提前两天开始准备。除夕当天四点开始做晚饭,杀猪、宰羊、蒸鱼。“今天是哪一天我都搞不清楚,这里哪像过年的样子。你看,像不像样吧”,谢民韬摆摆手道。
后来,我常见谢民韬在走廊尽头的窗边站着。我走近时发现,马路对面一家餐馆的招牌写着“湖南麻辣烫”。当我问他是否注意到时,他没有回答,只说:“麻辣烫,我会做。”他回忆起在老家湖南江华,烧菜用的是木炭,味道比用炉子用电要好。这个季节,烤火的时候,把红薯放在炭火里,慢慢烤,慢慢烤,直到表面结一层酥香的皮,他很喜欢吃那层皮。但来了深圳,他便再没吃过。
难以打出的电话
“小陈——小姜——”
听到这熟悉的声调,是什么人、什么事,我们心下早已了然。70岁的郑继军不止一次请求我们教他打电话。他神志清楚,但可能因为年老,就是搞不清楚手机的操作,甚至看不懂是不是充满了电。我们与他的所有互动都围绕“打电话”展开。巧的是,这一次我们被迎面走来的护理员“抓了个正着”。护理员对我们说一句“快走”,随即接过轮椅的把手,将轮椅转了180°,一把将郑继军推到两米外,便去忙其他事情。
郑继军手机里存着家人的号码。第一次教他时,郑继军说:“拨个号,看能不能打通。”我们有些惊讶,不懂为何会出现打不通的情况。而这个电话如他预料的,没有人接起。
“不接电话,就怕我烦他们。”
护理班长马婷婷说:“他女儿都要被他缠疯了,他家人把他送到这里来就是被他烦死了。我们不要顺着他要安抚他,要不他家人把他送到这里来干嘛啊。”
郑继军才来这里两三个月,护理员们便结合他家里人的要求,鼓励他尽量减少与家人的联系,融入养老院的集体生活。
郑继军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伴随着抑郁症状。负责他那层楼的沈林玉院长认为,郑继军所缺乏的,是一种需要别人更多关注的安全感,而一个护理员需要照顾五六个老人,不可能时时刻刻跟着他。“越是顺从他,他的这种情况就越糟糕”,沈院长说。
郑继军向我们抱怨道:“‘家规’不合理。不让我打电话,那我有啥事儿不能联系联系吗?你说,他们是不是不懂道理?”对他而言,养老院不仅难给他“家”的感觉,更是阻断了他与原先的家的联系。
郑继军平静时,也像其他老人一样,教诲我们;但他的情绪不稳,容易波动。
我们难忘第一次见他时的场景。“你们要好好学习,多实践,读原著:马克思著作、列宁著作、毛泽东选集、鲁迅的书……”他缓缓地念着,突然就哽咽了,眼圈泛红,眼里闪着泪花。我们不了解情况,一时也慌了,不敢再回答什么。好在社工慧琳过来“救场”,轻抚着他的背说:“郑叔,不激动,不激动。”
旁人看来只是闲聊的话题,也总会引起他莫名的情绪波动。情绪一波动时,他就如同婴儿寻求母亲的怀抱一般,给家里打电话似乎成了他潜意识里的需求。
郑继军的护理员将他推开后,我们刻意放缓脚步,郑继军推着轮子赶了上来。
我为难地说:“但是你也看到了,刚刚他不让我们教你。”
“他说了不算,你们教我用手机,这是义务。”
突然,他提出借我们的手机给老伴打电话的请求。推诿之间,他的护理员又悄悄走到了他的身后。护理员语气强硬地问:“你想干嘛?”
郑继军立即回答道:“她们实践(有这个课程,要教爷爷用手机)……”这是他提前编好的话术,但还没说完就被护理员打断了。
“你给家人打电话,你用人家的电话?你自己没电话吗?”
“我手机你也不让我打。”
“谁不让你打了?你经常打电话,谁不让你打!你一天天满嘴编话,我警告你,人家学生在这儿实习,要写论文,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没有吃没有穿还是咋回事,你需要啥你跟我说。”
“围巾。”
“你那儿有围巾。”
“我要大的围巾。”
“天儿马上热了,你冷还是怎样?”
“我不打了,不打了……”
“没有人阻止你打电话,知道没有?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护理员推着他离开。
自这场风波后,郑继军没有再让我们教他打电话,但他不再像从前一样主动热情地喊我们“小陈——小姜——”。
被安排的“家”
“老了,没权利了。”
 章萍房间窗户望下去的幼儿园 陈雪映摄
章萍房间窗户望下去的幼儿园 陈雪映摄
章萍摇着头说这话时,我才注意到她那枯干脸上的皱纹、苍白的嘴唇和凹陷的眼窝,想起她已93岁。
初见她时,她穿一双皮靴,走路还算稳健。相比这里许多年龄比她小的老人,她的健康状况要好得多。在这里,老人们被贴上的最基础的“标签”,通常是关于健康状况的——“失能”“失智”或“自理”。在养老院待了近一个月,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下判断:这是一位自理老人。
但身体上能够自理不代表对生活也拥有同样的掌控力,至少在选择居所这一点上,总由不得章萍自己。
“烦得很,住得好好的,又要搬。”2月9日这天,章萍异常焦躁不安。
由于院里楼层调整,她需要从三楼搬上四楼。她不喜欢麻烦护理员,也不放心让别人收拾,知道要搬“家”后,自己一点一点将东西拿出来包成一团团,大大小小十几个包裹堆满了房间里的两张床——这是她全部的“家当”。
她对于新房间的顾虑有两点——一是怕不能看到幼儿园,二是怕跟“神经病”住一起。
学习幼儿教育出身的董事长严敏,一直想做一个老幼共托的社区,在申办养老院约两年后,于2021年2月在一旁开办了幼儿园。老人和孩子常一起升国旗、做游戏,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动。但疫情爆发以来,幼儿园和养老院只能分开活动。去年入住的章萍没能碰上与孩子互动的机会,但她房子的窗户正对着楼下幼儿园,她很喜欢站在窗边往下望,有时候搬个凳子在那儿,站累了,就坐着。曾有一次,她发现楼下有个孩子与自己的重孙长得很像,她忙打电话给孙子,问电话那头6岁的重孙:“你想没想太奶奶?”电话里传来稚嫩清脆的声音——“想”。
章萍口中的“神经病”,是指失能失智老人。据班长介绍,三楼能交流的老人大概有三位,章萍便是其中之一。她刚到养老院时,曾与一位失能老人同住,每到换尿裤的时候,“那个味道受不了”,即便是晚上,她也要往房间外面跑。“要是分到跟‘神经病’一起住,我就出去,打滴滴去市政府!”或许这是她一时的气话,或许她真这样考虑过。但至少现在,这只是她与自己的抗争,愤怒而绝望的抗争。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安排着搬“家”,每次总是以她的接受终结。
章萍的老家在三百多公里外的梅州。老伴离世后,小儿子打电话劝她:“妈,现在全部都走了,你一个人在家里干啥嘛?以前你种东西卖了供我们上学,现在我们一个个都大学毕业出来了。你还种啥,不种了,你出来。”章萍就出来了,到了深圳。
2021年4月底,章萍几经周折,被儿女们安排住进福寿园。
 章萍收拾好东西在房间等待搬家。 许敏静摄
章萍收拾好东西在房间等待搬家。 许敏静摄
在福寿园,从三楼到四楼,她的居所仍被安排着。但这一次,她似乎不想再接受安排了。她打电话给二儿子:“最好疫情没有了,你就来接我,唉,我不想在养老院待着了。这里卧床的多、神经病多,我好怕……”
2月8日,量血压的医生告诉她:“你要搬家了,搬到四楼,这里要装修。”虽然不大情愿,但她似乎还未完全放心上。我去找她时,她热情招呼我进房坐,提起搬“家”的事,她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说是这个礼拜,没那么快,今天礼拜……今天礼拜二,管他呢。”正说着,她往柜子走去,执意要拿个苹果给我吃。
但第二天再见她时,她所有的不安都写在了脸上。她从别人那儿打听到,后天就要搬走。“后天要搬了,都不跟我说,你看我多少东西啊!我一下子能收拾吗?想过没有?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关于搬“家”的所有信息,章萍都是打听来的。
自2月9日始,便有老人陆陆续续搬上四楼。采访期间,不断有搬东西的声音传入章萍的房间。“人家都搬了还不跟我说啊!”令章萍焦躁的,不止是搬“家”日期的临近,而是这一天即将到来,自己仍像个局外人一样没有被正式告知。一直没有“选择权”的她,如今连“知情权”都没有了。
2月11日,章萍守在房间里,手里攥着一个黑色小皮包,一副随时要走的样子。根据她打听来的消息,今天就要搬上楼了。“可能上午搬,可能下午,我不知道,搞不清楚。”她的语气已由前两日的烦躁,转为无奈。这时班长突然进房,将她床上的十几个包裹堆到墙角,搬着房间里两张床中的一张出去了。
班长走后,章萍就站在她的这些“家当”旁,朝窗外的走廊望了好一会儿,像个局外人在看戏一般。
免责声明:我们注重分享,文章、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如有异议,请告知小编,我们会及时删除。
依据《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第12条,《信息网络传播权力保护条例》第14条/23条,即“避风港原则”,本文中部分图片及文字信息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行为请及时联系客服删除,本网不对内容传播行为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