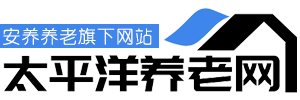【文/崔昌杰】
据国家统计局(2021)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比例18.7%,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3.5%,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人口老龄化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化在人口结构上的表现,其在中国家庭层面则呈现为一种“下行式家庭主义”(阎云翔,2017),即家庭作为一个天然养老单元的功能正在逐步弱化,那么我们该如何满足如此庞大的“溢出”家庭的养老照护需求(胡晓映、吕德文2022)?“养老服务的市场化”便是应对方式之一。
近年来,国家政策层面上有对养老机构数量与养老床位数的“增长计划”,各地各类养老机构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建立起来。但与看似“利好”的行业前景相比,关于养老机构的负面报道却也不绝于耳:“70岁护工过失杀害89岁老人,背后反映了中国老人的真实困境”(八点健闻,2021);“福利院护工连续掌掴痴呆老人,警方已介入调查”(澎湃新闻,2020);“高龄老人遭护工掌掴:3.5小时打57次,护工虐老引深思”(中国日报网,2018)等。
在这些报道中,民办养老机构无一不处于道德洼地。但正如吴心越(2021)指出,大众常常会将这些负面新闻的原因归结为护工的低素质,而忽视了具体照护实践过程中情景的复杂性。
本文便试图通过田野经验对此种“复杂性”进行简单的勾勒与说明,表明不仅是护工,家属与机构运营者也对这些负性事件的产生负有责任,并在对机构养老涉及的三个主体角色分析中,总结出机构养老行业的自身特质。

合肥:小朋友前往养老服务站开展“爱在重阳 情暖飞虹”主题活动。图源:视觉中国
家属:信息不对称与情感弱化
在机构养老实践中,家属虽然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照料劳动,但其仍然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维度介入其中,使照护劳动本身呈现出“护工—院民—家属—机构”这四方主体的互动与博弈状态。其介入也使得照料劳动更为复杂。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家属虽然购买服务却不亲自享受服务,无法做到服务购买与服务享受双方的直接交流,信息在多个主体之间流动。这使得家属对机构内的照料情况知之甚少,他们无法监督照料过程,也就是说,在照料过程中存在一种“信息不对称”。
因购买服务者(家属)与享受服务者(院民)的空间分离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购买服务者(家属)无法实现对机构的充分监督,享受服务者(多为失能失智群体)又没有监督能力。
因为家属对院民有赡养义务,因此对养老机构也应有相应延伸的监督义务。故而在购买服务后,并不意味着家属只有权利而没有监管责任,家属应当通过情境来进行判断是否应主张其监督权,这也是家属的责任所在。
同时,家属与院民的联结程度会直接影响到机构对院民的日常照料,但这种建构关系的主动权却主要掌握在家属手中。除了前文所提及的“下行式家庭主义”(阎云翔,2017)外,因为城市养老的“去家庭化”更快,被发展和理性的话语所统治,家庭养老缺乏底线保障机制,不仅法律保障的成本高,城市社会中也缺乏相应的社会机制,不似村庄社会中社会舆论等作为底线机制还发挥一定的作用(贺雪峰,2022)。
因此,家属可能存在的第二个问题便在于其对院民的漠不关心,无疑会使得养老机构内的照料生态不断恶化,诱发各类恶性事件的产生。
虽然说将父母送入养老机构也是践行孝道的一种方式,但一个普遍事实是:在院民进入养老机构之前,其已经对家庭照护者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身体负担与情感负担(吴心越,2020)。例如一楼的赵奶奶在被送入养老机构时,她老伴向我们诉苦:
“她也是老年痴呆,脑子时好时坏,特别容易乱跑,然后就找不到人了,前几天又是跑丢了,谁也找不到她,最后只能出动公安找,我心脏搭桥手术已经做了四根了,再也经不起刺激了......我儿子儿媳都有工作要忙,现在儿媳还怀了二胎,我又照顾不了她,那就只能把她送到这里来照顾。”
在已经对家庭造成较重照料负担的情况下,家属在将亲人交给机构代养时便已经出现了一种“情绪”和“疲劳”,只要被照料者在机构内“安全”生活即可。因此,家属和院民两者对于什么是“好的照料”本身是存在分歧的。
S机构三楼的部分可自理老人在与我日常的交流中都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中流露出对“交流”“陪伴”和“自由”的向往。不过当前绝大多数的中低端民办养老机构仅能为老人提供底线生存照料,再高一层次的精神与情感照料远未实现。
但在院民的家属看来,他们既希望养老机构是服务者,也希望其可以作为一个管理者,这样才能不让院民“给自己找麻烦”。
由于被送往养老机构的院民多为失能失智群体,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对他们的照料要求较高,尤其是精神上的失能半失能院民,如果居家照护,家庭要付出较重的照料成本,但处于发展阶段的子代家庭又无过多劳力与精力进行看护,便不得不将其送往养老机构,如王奶奶的女儿直接将其称为“我们家害人精”,也是因此才将其送往S机构,几乎不来看望。
故而机构除了提供服务以外,还必须承担管理职责,以减轻家属负担。这种“不找麻烦”式的动机也在管理者口中得到了证实:
“如果你到一个养老院,发现这个养老院打出的宣传标语是安抚老人,关爱老人,总之就是一切顺着老人的意思,那就千万不要去这个地方。因为这里就像一个学校,而这些工作人员就像是老师。如果一个养老机构,他会批评,会斥责,那说明你的老人送到这里一定会被管理的服服帖帖,也一定不会给你(家属)找很多麻烦。”
随着院民在机构入住时间的延长,院民失能的程度会越来越深,家属来看望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少(李丹、白鸽,2020)。甚至有的家庭在院民临终前一两年都极少去探望,也不在乎机构内发生了什么,只要老人“安然”活到去世即可,这或许是家属和护工之间的“默契”。那么这无疑是助推了机构内的种种不规范现象,只要不危及院民生命,机构的种种照料方式即是“合理的”。
“有的时候我们晚上,老人要死的时候你要经常去看……好比说他一死,你就要赶紧告诉家属。而且经常还是死了之后才告诉,在这里都是那样的。”
护工:被挤压的道义感
除护理对象外,护工是照料劳动中最为重要的主体,因为护工充分参与到了照料工作中,能够充分掌握自身服务供给以及机构其他服务供给(如饮食、娱乐项目等)的状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拥有监督机构老板和机构运营的能力。因此,护工能动性的发挥是院民照护质量得到保障的关键。
当然,护工本身也需要适度的规范和规制,因为在照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暴力与伤害的可能。但问题可能并不在于国家或市场在关于护工照料服务的规范性上不足,因为无论是何种规范,其遵守与执行都离不开护工自身的道义感和责任心,故而在此处主要探讨护工道义感的来源及其被消解的原因。
在物质资源约束较强的背景下(如S机构极限压缩院民生活质量、设法降低护工成本,其实多数机构都会存在压缩成本的做法,只是程度不同),护工的情感和道义将会作为改善照护质量的重要精神资源。总的来说其情感和道义可能来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尤其是一些理性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农村护工,会对弱势群体产生怜悯之情,这是自然感情流露,乃人之常情。
第二,基于与护理对象长时间的的互动和相处,在互相接触中产生道义感。
“我在第一家当时还有3700,我去了第二家才给我3500,当时我就去找他们老板去了,最后我做了一个月我就要走,当时有两个聋子婆婆,我对她们特别好,比对自己的老妈还要好,我一走他们两个哭的啊,非要跟我一路走。老板没办法了就非要留我,不要我走。”
第三,基于反叛。这是因为老板和护工的激励机制不一样,因此对待院民的态度也不一样。前者是总体利润激励,后者则是计件工资激励,老板可以通过压缩成本实现盈利,但护工只能依靠照护的老人数量获得提成,一旦老板极限压缩成本,其在损害老人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必定会降低护工的劳动体验感,同时催生其道义感。
“她光说大话用小钱,她光说大话。像那样对自己也不好,他们天天三餐,吃香的喝辣的,一点事都没得还去酒店吃饭。他们天天晚上都出去,有的时候还去XX那里吃。天天吃香的喝辣的,把我们这些人坑死了。那别个养老院,什么节日都发钱,一大早就送过来了,一大早就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啊’,在她这里就没的,哪个人都不念她。”
但在现实中护工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往往面临着多重挤压:
首先,在面对“不在场且不信任护工的家属”的指责时,其道义感会消解。上文提及,养老照料工作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而机构老板往往会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离间护工和家属的关系,使得原本有动力提供较好照料服务、有渠道监督机构的护工被排斥在服务状况改善之外。
“比如说家属给老人买的肉买的生的,拿上来让护工做熟了给老人吃,结果老板都收走了。前几天经常下去闹那个爹爹,他的家属给他买的东西,什么洗衣粉啊,洗洁精啊,她把那个洗衣粉,这么大一袋洗衣粉,她给掉包了,换的水货......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护工干的。”
“有的家属就很不领情,认为我们是想赚钱,你说说良心话,我们干嘛要这点小钱?叫他们自己去外面买,他们不领情,那就院长高价卖给他们吧,质量还不好。”
其次,护工的道义感也会因为与被照护者的城乡差异与矛盾所消解。既有文献均指出照料者与被照料者往往处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苏熠慧,2011;陈义媛,2013;吴心越,2021),那么当身处两种不同的经济与文化环境时,差异越大,二者的融合成本就越高;且二者的年纪往往都较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都较难再调整;再加上市场关系的双向选择,便会使得双方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能力与动力均不强。
“有一个婆婆照顾了1个月,那个婆婆是蛮怪的。一天到晚她总是搞点什么东西在床上,冬天的时候还总让我晒,又大又重,一晒晒的又多。后来我回去过年,做了一个月,过了年之后就没有再回去了。这个婆婆好比说就是她发现有一点东西,她都说是你没有搞干净卫生。(问)我为什么不搞干净?你说我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洗?我还怕浪费你的水,你说是不是呀?这又不是我出钱。上面有油,我还是用热水洗的,还说我没洗干净。一点不舒服,她就说这不卫生那不卫生,是这样的婆婆。”
第三,被机构行政管理者的“同理心匮乏”所消解。前文提到机构老板与护工所属的激励结构是不同的,但机构管理者与护工的激励结构也是不同的,不同于护工的“计件工资”,管理者是“计时工资”,按时上下班,记录护工考勤与管理突发事件即可。
但问题在于,由于管理岗位在记录护工外出等考勤时较为机械,且在处理突发状况时完全是目标导向的,未能充分考虑到护工当时所处的具体情境,久而久之,护工为表达不满,便在许多照料事项上消极、应付对待,从而恶化了院民的照料环境。
“她(S机构管理人员)走了才好,她是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座大山。什么都看不惯,什么都想说,她一走我们就解放了。她哪里来这么多事情?我跟她说我在上厕所,我在厕所里面。没有看见我,她就说没有人照顾这些孩子。你说她好多事都是这样。什么事情都是她说别人。她不晓得你的意思,饱人不知饿人饥。”
第四,护工被拥有过度盈利动机的老板进行剥削,加大照料压力,进而消极怠工。随着在市场化环境中浸染时间的增长,在面对老板的剥削时,护工要么选择“一走了之”,要么“默默忍受”,做出何种选择是与护工在职业结构中的地位密切相关的,年轻的护工职业选择空间大,但低端养老机构中护工年龄一般都在55岁及以上,这便极大地限制了她们的职业选择,在机构出现一些问题时仅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自身在照料压力过大时也只能默默忍受,无疑会加重护工在照料过程中的负面情绪,为负性事件的产生制造了条件。
“我们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老了不比年轻人,院长说我们,我们是一句话也不敢说,她对我们是想抓就抓,想放就放,不过,我们也可以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但问题是我们要是一下子走了又找不到新的工作,怎么办?这个工作老了就是不好找,它就是个体力活呀,我们老了哪里有人要啊,不比那些年轻的护工。”
以上种种原因,都会在情感和道义上消解护工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最终代价则是护工“道义感”的下降,从而致使照料质量下降。但这一后果却需要由被照料者即院民承担。
事实上,在养老或者残疾儿童照料领域,照护对象处于半失能甚至失能状态,购买服务者即家属又因为不在场而无法提供规范和规则,作为剩余劳动力的护工往往又会在多个层面上导致其“道义感”被消解,也就更无法成为规范和规制机构(老板)牟利的力量。因此,在这一照护领域便很容易出现不规范的行为。当然,具有强盈利动机的老板更有可能加剧不规范行为出现的可能性。
老板:最大盈利动机
在S机构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其作为低端民办非营利性机构存在着严重的过度牟利问题,在家属面前,机构表现出“一切为了老人”的态度,但在背后却大肆敛财,损害院民利益。
在田野中发现,民办养老机构有动力、有渠道进行过度盈利。不仅能通过“巧立名目”(利用政策套利,骗取政府补贴;与定点医院合谋、与殡葬”一条龙”合作,拓宽营收渠道;项目收费与定价混乱)与“侵占财物”(将慈善捐赠挪作他用甚至进行出售;扣留护工证、克扣护工岗位补贴;偷窃和侵占院民个人财物)进行“开源”;也通过“压缩必要成本”(极限压缩饮食成本与清洁成本,产生饮食安全、卫生清洁问题)与“压缩人力成本”(家族式经营与培养“心腹”;并克扣、剥削护工)进行“节流”,从而直接损害机构内院民的个人权益,在机构整体上便已经营造了一种灰色盈利的氛围。
下表是笔者在田野期间根据S机构部分公开数据以及访谈得知的信息,对机构收入支出情况所作的汇总,估算的结果也在田野中被相关报道人进行了证实。
“她(老板)的弟弟和我说‘我的姐姐极有钱......’。这个老板搞养老院搞了很多年了,之前是在XX搞,现在在这里搞,她有钱着呢……每年至少能靠这个养老院赚八十几万,他们一家人什么都不做,都能靠这个活下去。”
这109.68万元即为S机构每年可供分红的利润。由于院长及其家属占有机构50%的出资额,其每年可得利润分红约为55万元,再加上36万元/年的工资收入(这是因为老板还将五个家人安排在机构负责管理,每人每月5000元,每年便是36万元的工资收入),那么院长每年毛收入约为55+36=91万元。与报道人口中的数据大致吻合。
具体的牟利行为,在此仅就饮食方面举例一二:
“这里哪有什么好肉啊,全部都是冻肉,而且是她联系好的猪肉加工厂那边剩下的边角料,你没有发现这些肉都是一块一块的碎肉吗?根本不是什么肉,里面还有脆骨,甚至还有淋巴结,就这么运回来了。都是猪肉加工厂加工一整块整块,然后之后剩下的。”
“这里的银耳汤不要喝,我们从来没喝过,因为每次老板一进都是进好几大包好几大包放好久,如果发霉的话,再取出来清水一洗就可以吃了,你是年轻人,吃这个对身体很不好,以后都不要再喝了。”
甚至还存在为了节省燃气费提早关火导致米饭经常夹生、坏掉食材继续使用的现象。
与通常学界论及的养老机构普遍营收困难不同,我们从上表中可以发现S机构的仅靠五十多位院民便可实现年入近百万的收益。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前绝大多数养老机构还在处于成本回收阶段。
由于机构老板是“总体利润激励”,一旦前期的建设成本回收,其便可以实现盈利,成本越是压缩,资金回收越快,机构也就越有动力进行压缩,尤其是收回建设成本之后,其盈利水平可观,如S机构。
但如果只考虑资金回报,势必会制定超出现阶段老人实际消费水平的价格定位,或者机构也可以盲目的降低成本,但低成本运作带来的往往就是服务风险。
乱象的背后,是当前制度层面的监管缺失。既体现在法律制定层面,也体现在具体监管的操作层面。
首先,我国涉及养老行业监管的规范性文件虽然较多,但多为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缺少专门性的法律规定,且立法层级相对偏低。
我国养老行业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如《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的基本立法;二是包括民政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部门规章;三是行业标准类的标准化文件(张再云,2015)。
我国现有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虽都对民办养老机构的监管进行了一些规定,然而,其中大多数为一般性规定:要么责任和义务明确,但内容不够具体;要么只进行实质性规定,却缺乏程序性规定,导致法律适用性较弱(李璐,2020)。由于制度的规范性和权威性得不到保证,老年人的权利也很难得到保障。
虽然逐步出台了一系列养老行业的行业标准,但这些标准对于养老机构的约束力是有限的。在这里仅举一例:例如国家虽然规定了机构在护工配备上的具体比例,但在多数养老机构仍是无法达标的,一方面原因在于护工招聘存在困难,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在于机构为压缩成本,减少护工数量以便进行盈利。

浙江台州:养老中心为85岁以上老人免费提供午餐服务。图源:视觉中国
如在S机构,每一位护工人均要照料近11位院民。由于养老机构是一个较为扁平的社会结构,如此多弱势院民在进入养老机构后便有成为“照护”中心的动力,会不断地试探从而打破护工的照料底线,护工由于面临繁重的照料任务,无暇顾及所有情况,那么在两个层面上就会促发恶性事件的产生:其一,院民为竞争护工注意力,会做出自我伤害的举动;其二,护工为完成如此繁重的照料任务,便会采用一些“非常规手段”。
其次,由于养老机构在设立时需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其在行业性质上也归属民政部门管辖,但涉及到具体监管事项的行业标准时,民政部门却无管辖权(李璐,2020)。监管主体职能模糊已经构成了当前养老行业监管的重要阻碍。民政部门虽然具有一定的监督职能,但由于其在卫生、饮食、物价等很多方面的专业性有限,便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监管失范。
这里以养老机构的饮食服务监督为例:
“明天你早上五点半不能到厨房了,因为今天下午民政局的人来查的时候,到厨房发现厨房的监控被一个破布蒙住了,上面还扣了一个帽子。这是查得到的一个问题,民政局说要把监控摄像头打开,因为厨房重地,不是厨房工作人员不得入内,所以说明天早上你不需要去厨房帮忙了,而且不仅是早上,白天的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能进厨房。”
DCZ:那这些碎肉没有人监管吗?
EHG:他放在冰箱里面谁看得见呢?哪里会有人监管?
DCZ:没来检查过吗?
EHG:从来没有。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加深以及深入和养老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民办养老机构的开办数量也在直线上升,民政及其他相关部门应接不暇,导致对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过程监管多流于形式。
正是由于我国在关于民办养老行业上的“重准入—轻监管”,间接导致了近年来民办养老机构事故与纠纷频发,民办养老机构的行业声誉进一步下降,最终陷入一种低入住率的恶性循环(关信平、赵婷婷,2012)。
机构养老行业的自身特质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在呈现具体的田野经验之后,简单勾勒出机构养老行业的特质。也正是由于这些特质,使得养老机构容易发生负性事件。
(一)微观:特殊小社会
作为一类寄养机构,养老院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机构内生活的大多是失能、失智、残疾的边缘群体,即便是生活可自理的老人,在机构内也普遍被认为是与子女闹矛盾或因为给子女造成了负担从而“自己想”住进来,在护工看来这些均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也即是说这些群体在外人看来其社会化程度是普遍偏低,或社会化程度处于一种“退行”状态,与家庭的情感连结也较弱。
其次,这个“小社会”的结构整体十分扁平。仅包含“院民—护工—管理者—老板”四个层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仅包含“院民—护工”两级),在院民一开始进入机构时,对于院方来说,院民都是相对均质化的服务者和被管理者。
第三,护工、机构管理者与老板这三个层级的激励结构也是不同的。对于护工来说是“计件工资”:其照顾老人的数量决定了其工资提成;对于机构管理者来说是“计时工资”:他们只需按时上下班参与管理即可;对于老板则是“总体利润激励”:如何利益最大化。在这三种激励结构之间存在着一些张力,也会因此对院民照料产生一些影响。

(漫画)北京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2.47岁。图源:视觉中国
(二)中观:信息不对称
在S机构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当有老人被送入养老机构时,机构与家属必须签署《代养协议书》,之后养老机构便会安排具体的护工负责照料新进院民,家属则在经济上起担保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机构养老这一行业的“供给—需求”链条总体较长:购买服务的是家属—享受服务的是院民—供给服务的是护工—日常监督护工的是机构(也即是说,家属和多数失能失智院民是无法有效监督护工的日常工作的)。这就导致养老服务行业具有“强信息不对称”特征,此特征也会导致机构养老行业的市场交易成本变高。
(三)宏观:非正规经济
首先是在立法层面:我国涉及养老行业监管的规范性文件虽然较多,但多为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缺少专门性的法律规定,且立法层级相对偏低(张再云,2015;李璐,2020)。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关于养老服务标准的统一规定(金晶,2021)。
其次是在实操方面:具体便体现在监管主体的“职能模糊”(李璐,2020)。也即是说,虽然在行业性质上规定由民政部门负责管辖养老机构,但在具体涉及到卫生、饮食、消防等层面,监管权又被分散在了各个部门,这就会产生监管机制不明晰,跨条线协调困难的问题。民政部门虽享有名义上的监管权,但欠缺专业性,容易产生“小马拉大车”的问题。
最后在行业的一些运作方面:多数雇工都是未经培训的农村低龄老人,且大部分养老机构均未与护工签订劳动合同(吴心越,2021)。也即是说,在服务者层面本身就缺乏正规聘用,门槛低、就业灵活。与此相对应,劳动者也是缺乏保障的,也存在就业不稳定特征。
即是说,在宏观政策层面,国家在这一领域没有提供足够的规则和规范,法律越是模糊,监管越是缺位,就越是存在灰色空间,也为机构内的一些负性事件提供了制度温床。
总结来说,机构养老行业分别在微观、中观与宏观这三个层面上存在着一些特殊性质。在微观上的“小社会特性”,中观上的“信息不对称”与宏观上的“非正规经济”,三个层面的特质使得照料事务本身相对复杂,也会与具体照料服务中的各方主体互相纠缠在一起,制造更多张力与矛盾。也正是因此,照料劳动的具体场景,本身是复杂的。
小结
在以上三个特质的影响下,机构养老行业在规则化和规范化层面会存在能力和动力不足的问题。事实上,在养老或者残疾人照料领域,由于照料对象处于半失能甚至失能状态,而购买服务者即家属又因为不在场而无法提供规范和规则,护工的道义感又容易在机构内被消解。
因此,在照料劳动中就容易出现不规范的行为,具有强盈利动机的老板更有可能加剧不规范行为出现的可能性。种种因素加持之下也就加剧了养老机构负性事件出现的可能性。
因此,这一领域对规则具有强依赖性,国家在输入资源的同时也应该输入规则,适度的规范化和正规化,有利于弱化主体间各种博弈,也能够约束老板的过度盈利行为,否则公共资源投入后就可能被非正规经营所吸纳,护工的劳动过程也会因为这种非正规经营而被影响。
但也应当指出的是,在制定统一的法律或监管标准时,要警惕政策目标的技术理性化,在日后养老机构管理政策日益专业化和科学化的同时,需警惕掉入技术化的窠臼。仍需指出的是,管理规范化是有成本的,不管理规范也是有成本的,而成本最终都可能要由被照料对象承担,因为规范化后照料成本或许会提高(家属在选择养老机构时,价格本身是一个重要标准),但不规范化,院民的利益又面临着被严重侵害的可能性。
现实情况是,规则化和规范化往往意味着某种成本上升,机构就会倾向于利用这种不规则和不规范来压低成本,从而最大限度的获得利润。也就是说,非正规经济为过度盈利产生营造了一种制度空间,也是因此这一领域对规则具有强依赖性。
故而,国家在输入资源的同时也应该输入相应的规则,否则不仅公共资源在投入之后可能被此种非正规经营所吸纳,而且机构内院民的个人权益也会被极大程度地侵害。
免责声明:我们注重分享,文章、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如有异议,请告知小编,我们会及时删除。
依据《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第12条,《信息网络传播权力保护条例》第14条/23条,即“避风港原则”,本文中部分图片及文字信息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行为请及时联系客服删除,本网不对内容传播行为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
本文地址:崔昌杰:为什么养老机构那么难做?